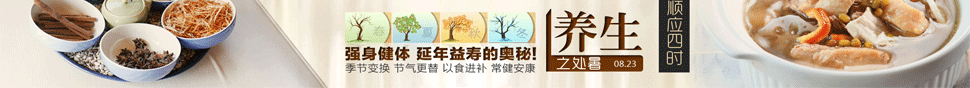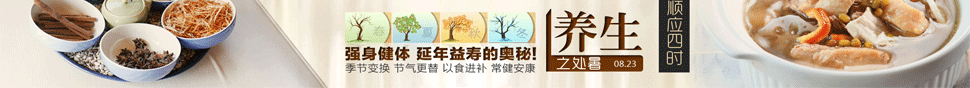北京中科医院几级 https://jbk.39.net/yiyuanzaixian/bjzkbdfyy/mbbdf/来到甪直,所有人的第一个问题是:这里为何叫做甪直?对此,民间有多种答案。一种是,因为有六条河流从镇内穿过,三条横向、三条纵向,这三横三竖的河道交织一起,构成一个“用”字,沿着镇的一侧流过的吴淞江就像个“丿”,这样的形成一个“甪”字,所以唐代时改名为“甪直”,“甪直”,“甪”的每一笔代表着小镇的河汉一条。又有一种答案是,相传古代独角神兽“甪端”巡察神州在地,路经甪直时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,因此长期落在这里。甪直因此得名,而且从此没有战荒,没有旱涝灾害,人们年年丰衣足食。不论名字怎样得来,“看水乡,逛古镇,不可不去甪直”。与其他江南水乡古镇不同,龙形水网的甪直古镇,是因寺而兴庙,走进它,就像走进乐府诗歌中。河撑起小镇的主体结构,桥成了小镇人往来交通核心。“水巷小桥多,人家尽枕河”,宋元明清四朝石桥原本有72麻,原是“五步一桥”;现在只有41座,却也造型各异,拱形的、圆洞形的,单孔的、多孔的不一而足。石阶埠头下,婀娜多姿的船娘声声呼唤着客人游湖观景。河两岸是刻有凤凰、麒麟、花朵等各式图案的河栏,不论晴天雨天,这里总是有人依偎聊天,装饰着河上人家的梦和想象。甪直镇现有主街道9条,街道两旁店铺林立,街面都以卵石及花岗铺成。店家敞开着门板,摆放着精心制件的橙黄的南瓜糕、酥脆的鞋底酥,赤红的酱萝卜、碧绿的薰青豆,香味弥漫了整条街。民房大多临河而筑,前街后河,人在桥上走,船在水中行。这里的民宅,无论临河还是临街,都是黛瓦粉墙、木门木窗、青砖脊、出檐平直,大多为明清时代的房子。明代的宅第建筑,有严格的规定,清代初期继明制,到了后期,制度逐渐放宽了,只要屋主手中有钱,就可以随心所欲、自由建造。目前,这里保存得最好的明清住宅,就是大名鼎鼎的“萧宅”和“沈厅”了。而最大的宅第,当推明代元曲家许中翰的“梅花墅”。它纵深若干进,各进为三间,从里到外是平行三条轴线,另有鱼池、环廊、小桥、竹林、梅园,环境优雅,装饰精美。难怪明代诗人钟惺在《梅花墅记》中,称赞它:“不亚于拙政园”。古银杏树也是甪直古老的象征之一。目前镇上有银杏树7棵,其中在保圣寺中四周有4棵,最大的一棵已有年的树龄,高50米,树身三人合抱也围不住,虽经千年风霜,仍挺拔健壮。著名教育家、文学家叶圣陶先生在甪直执教期间,因之写下散文《高高的银杏树》,称赞它“形象高大,意志坚强,气魄宏伟”。叶老去世后,他的骨灰按其遗嘱就被安放在四棵银杏树下。除了古桥、古街、古民,这里的名胜古迹更是星罗棋布,虽然历经历史的磨难,但细细看来,仍能找出它们当年的风采。“万盛米行的河埠头,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船。船里装的是新米……”叶圣陶先生笔下的万盛米行,幼时便因书本被记在心里,本以为虚构的,不想它就在甪直古镇。于是小说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中,这农民摇撸粜米的场景也越发真实起来:埠头上随水荡漾的小船,账房里带铁钩的秤、量米用的斗,甚至账房先生的坐椅和柜台,竟和少年晨读时的想象如此贴合。“甫里繁华照市明,况多人物负才名。”不知道是甪直水乡的美景造就了这些名士,还是这些名士成就了甪直的名声,总之甪直背后是一长串名士。首先是叶圣陶先生与吴东地区首屈一指的老字号万盛米行,当年甪直及周围十多个乡镇的粮食集散中心,若没有这位文学家、教育家的笔,恐怕不会进得中学教科书,也不会因此蜚声海外。年后,27岁的叶圣陶在甪直甫里小学执教5年,他“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”的教育思想应该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吧,从而开启了他后来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,小镇因此记住了他,街上随便问一下,人们谈到他都是敬佩和尊重的。叶圣陶纪念馆和别处的纪念馆相比,似乎也要不寂寞许多。另一位甪直名人也享有同样的殊荣,他便是王韬。因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而背井离乡、流亡香港的王韬,是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人、西学传播的主将之一。他中年漫游西欧,是中国知识分子实地考察欧洲第一人;此后,又创办《循环日报》,被林语堂称为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。他的纪念馆在城区的幽深处,连同陈列室、故居、弢园在内,共有平方米,气势是十足的宏壮。虽然当地人并不见得知道他的意义,但不妨碍对他的尊重。忠厚传家久诗书礼仪长,一家人的门联反映了用直人的价值取向。晚唐诗人散文家陆龟蒙则直接开启了甪直的文化渊源。号称甫里先生的他,屡试不第,后来虽做了一些刺史幕僚这样不痛不痒的小官,但总是意难平。于是和历史上多数失意文人一样,这位颇有才情的诗人便在甪直置办了几百亩土地,一心想做个快乐地主。可这水乡泽国哪里是良田,大雨之后,收成稀薄,甫里先生也能想得开,便养鸭为乐。闲时常与农民一起耕种,甚至研究起农具来,还发明了牛犁,出了《宋朝经》介绍农具。古书记载他:“有田数百亩,屋三十橱,田苦,雨潦则与江通,故常苦饥,身备插袜刺无休时”,可见这个地主并不轻松。不过因为他那些美妙的咏景诗,投资失败的他也就成了这古镇文化的开创人,此后皮日休、罗隐等文人学士慕名而来,与之相游唱和,盛极一时。甪直浓郁的人文风气因此渐成。陆龟蒙的墓便在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一的保圣寺内,相伴这爱鸭之人的还有“斗鸭池”,颇有些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”的味道。看过小桥流水,体味其中清风明月。甪直的感官是如此完美,连味觉也不曾放过。它独树一帜的饮食文化在江南也享有盛誉:“甫里鸭”的名字暗示着它和年前养鸭为乐的甫里先生有若有若无的关系,为了强调这一点,“甫里蹄”还取了别名“龟蒙蹄”。许多宣传材料里,更煞有介事地指出甫里鸭、甫里蹄源于陆龟蒙的菜单,它们是诗人隐居甫里时宴请各地来访文人墨客的主菜。两道色泽清爽的江南名菜竟也沾染了如此多的文化气息,穿肠而过的酒肉竟也散发着古韵,游人自然口齿生香。甪直农村妇女的服饰,也是古韵悠然。此处的农村妇女,历来以梳髻头、扎包头巾、穿拼接衫、拼裆裤、束裾裙、着绣花鞋为服饰的主要特征,很富有甪直特色的水乡风格,因此被称为“苏州的少数民族”。今天,西部地区40岁以上的妇女,仍保留着这种传统特色的民族服装。古镇区不过一平方公里,绕城一周不过“一袋烟”的工夫,难以想象这曲折的窄巷中竟走出如此多的文化名士。也曾有过仓惶夜奔,也曾有过饥寒所困,这里记录的历史和现实却都如穿桥而过的溪流,平缓安详;一如那吴侬软语,不急不躁。也散着书卷的韵味,也散着墨香,就连路边普通的茶馆一间都会取名“未厌”。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
http://www.qilinzhang.com/qlzjg/12520.html